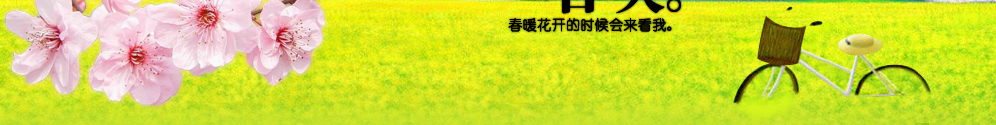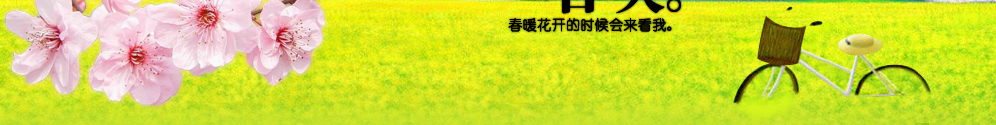当月亮越发洁莹,夜风更加清冷时,我就知道夜已经很深了。
她突然不自禁地打了个冷颤,就像秋雨中哆嗦了一下的小鸡一样,我心中突然涌起万股的怜意。
我只有一件衬衣,我总不能除下给她披上,况且她也不会要,所以我只能迟疑着道:
“你冷了吧?如果你不介意的话,你···你···可以···可以···”
我终于还是没说出来,叫她偎在我怀里无异宣告自己正是一个流氓。
“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,说下去啊。”
她望着我的双眼显得热烈,但似乎也透着一丝羞涩,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看穿了我的心意。
“我···我想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回去了吧?”
“我从来没有晚上来过白云山,今晚的感觉很好,你···你就再陪我十分钟吧。”
她的双眼有些暗然,不知是否因为她又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夜空之故。
不幸的是从白云山回来的第二天她就受凉病倒了,躺在床上那种楚楚可怜的神色直让我看着心酸。
摸摸她的头部冻得我直哆嗦,人人都难免会感冒,但怎么她就像从地府里钻出来的?
“别···别担心,我自小就从骨子里透着寒气,吃些感冒药,过两天,只过两天我就没事啦。”
她微笑着说,但那种微笑透着悲意,就跟你摸女人的手却像是摸到一堆沙子一样,绝不会是舒服。
“真是这样?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,我就请两天假陪你吧。”
如果我真的放心她一个人在这,那做父母的也该放心一岁的婴儿独自在家不用大人的照顾。
她眼中透射出谢意,这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啦,就跟摸风却像摸到沙子一样实在。
这两天来我就像做丈夫的服侍病中的妻子一样尽心尽忠,而且还有对妻子的那份怜爱。
我有时坐在她床头讲些笑话、童话给她听,当然有时还讲些假说,但我并不知道美丽不美丽。
这种情形虽是带点悲意,但也是十分温馨的,就跟一对老夫妻正在走他们的最后人生之路一样。
但她的精神并不好,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俩却是相对无言,默默的眼神似是交流着千丝万缕的情感。
我突然发觉,我现在跟她在一起时除了给她欢乐外,更是添了一份关怀,从未有过的关怀。
“明天你就可以上班啦,我现在已没什么大碍。咳···咳···”
她轻咳了数下,不知我有没有眼花,她吐出的痰似乎有些血丝。
“你真的没什么事?怎么你的脸看起来比前两天更白啦?”
“白不好么?不知有多少女孩子在羡慕我的肤色呢。素手冰肤、晶莹剔透,说的都是白啊。”
“听你一说我就暂且将‘安心’留在这,但你要记住我俩现在已是‘一家人’,有事要打电话啊。”
“你既不是我的丈夫,当然更不会是我的父亲,怎么今晚你就那么罗嗦?”
她虽是嗔骂,但我怎会看不出她心底的谢意,所以我开心地看着她,甚至在轻托着脸倒又似在欣赏。
可第二天下班后她并没跟往常一样把门打开,我的心不禁往下沉,虚无的沉落伴着无限的慌乱。
当我进了屋后也没她的影子,我的心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虽然房子里的一切都摆得整齐并不凌乱。
“也许她只是上街买些东西罢了,我怎么无事白忧愁,有事愁也休来啦?”
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的,似是在安慰自己也似是在解释她的去向。
但我知道我的猜测是勉强的,我相信你没见过该要吃饭时还要离家的女主人,当然除了意外。
意外?想到这,我的心不安地猛跳了一下,因为我回来后已干坐在那两个小时啦。
十二点,时间根本就不顾我难受的心情咚咚地赛跑似的冲到了十二点。
我猛地发现自己是那样的无助,我根本只知道她是慰安,而且现在也不知篮拔堪菜跄懿盘眉?br>
也在这瞬间,我突然感到她对我是很重要的,或者说是她已成了我的一部份,似是手一样离不开她。
我的心在痛,思维在麻乱,整个人似有一种莫大的恐惧,可是眼泪偏偏就是在打转也转不出来。
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呆在这等待,无论如何都要到外面找找她,虽然外面很大而她很小。
我就像一个无助的肓人,也像一个在游荡着的孤魂,既不知前方的路也不知如何寻前方的路。
我很希望她的影子突然灿笑着出现在我眼前,给我惊喜,然而更多的是一条野狗窜出来给我的惊吓。
街灯暗然,但它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我黯然的心情更惨淡,惨淡得已不足以支撑我沉重的躯体。
所以我坐在街边上,那怕风已把我吹得摇摇欲坠,雨把我淋得浑身湿透,但我都没有躲避的念头。
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心际的失落同样是和风一样的虚无,伤痛的泪水根本就比雨水还要肆虏。
风雨虽然仍在交加,但天已亮了,穿梭的人群已不再令我有一个安静的环境。
我拖着极疲惫的身子回去了,就像一股秋风卷起的落叶一样带着无比的凄凉。
门打开了,但不是我开的,开门的正是令我一晚都失魂落魄的慰安。
“你···你终于回来啦,你没事吧?以后就算有事也该要先说一声,那怕只是留张条子。
你该知道,如果你从我身边丢了,我虽身上不会背着十字架,但良心终会伴我···我终老。”
我冲动地握着她的手,声音有些哽咽,然而心中却是一寒,怎么她的手那么冻,难道是我手上的雨?
“你···你为什么那么紧张我?难道···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恨我?”
该是因为我手上的雨水也令她感到了寒意,要不怎么她的语调也有些颤粟。
她说的对啊,是她令我六神无主和流落街头的,我该恨她才对,为何现在见着她却只有喜欢和欣慰?
“你没事就好,干吗要恨你?做父母的见孩子的病好了,可只有高兴难道还会责怪他得这种病吗?”
我说出了我的理由,但我知道我的理由实在勉强,勉强得连自己都几乎怀疑自己是在说谎话。
我想,我不恨她也许是我已将她当成了我的好朋友,我不想失去她当然也就不能恨她啦。
可是她呢?她是否也有我一样的感觉,那怕只有一点点?
第二个周未不声不响地又已来了,像是踩着风裹着云悄无声息地来了。
现在我跟她就并肩地坐在江边的草地上,静静的,轻轻的,那种柔情甚至比江风还要温柔。
“嗯,送给你的小礼物。”
我将我做了一整天的纸玫瑰花拿了出来,是用彩纸做的,我虽然做得很细心,但做得并不很细致。
我本来是想送支真玫瑰给她的,可那样的话似乎脱形落迹,还是做成礼物借物寄情的好。
也许可以这样形容,就跟一个眼光闪烁的人,如果戴上了墨镜自把对外界的不安通过屏障变得安心。
“你做的真好!可惜就差了些香气。”
她说罢拿出她的香水滴了两滴在纸花上,当真很香,甚至还有些甜,也许是我对她赞美的反应。
“为什么就一定要惟妙惟肖呢,难道你还想逼真得明天它就要谢了?”
我说得很认真,但这根本就是白说,我的严肃一点都盖不住她吃吃的娇笑声。
“我看你的双手并不比我的纤细,但怎地做起这些东西却又比我灵巧得多,难道你是一个女儿身?”
“不能因为我比你强就诋毁我的人格,这样好了,如果你眼红手上的功夫,下回我就用脚做礼物。”
“嘻嘻,你用脚做礼物?难道你的脚还会比手灵巧?但我先声明,如果礼物带有脚臭我可不会收。”
她一脸的不信与好奇,可惜我现在也不知自己用脚能做出什么来,所以对她的嘻笑只能以苦笑回应。
“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,我可不想跟上一回那样再服侍你啦!”
“再等一会吧,你看我还有很多的小吃都没尝遍呢。”
看着她在风味小吃档前的那种馋样,我相信她以前没到过这些地方,所以我只好陪着她。
她终于尝遍了,非但高兴,甚至满足得舔了舔唇边的液汁,那样子就跟刚吃饱的家猫一样。
所以我说走时她已没半丝的遗憾,只是我心中有些不安,原来我今晚带的钱实在少,只剩下一块钱。
“啊,那么巧!今晚我也忘了带钱包,也只有一块钱,难道那么长的路我们要一步步走回去?”
她的神色绝对看不出有半丝的说谎,所以我的脑子已飞速地盘算着。
“没关系,我有办法,当然这要看我们的运气,最主要是你的运气,我的运气向来都不好。”
“嗯,我相信你会有办法,到时我就看你的好戏,我虽不是‘嫁狗随狗’,但可是跟你随你呵。”
她的脸突有一丝红晕,昙花盛开一样,所以我陡然间觉得作出这个承诺的压力,很重但又心甘情愿。
我在路上捡了一片报纸在手上摆弄着,她只是很认真地看着我,并没有问为何。
她实在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,该不问就不问,跟她生活在一起,非但快乐而且很舒服。
已经来到公共汽车站,我侧头对着她道:
“你跟在我后面,就跟往常一样,别紧张,万事有我担当。”
说罢,我已当先上了汽车,将刚才自己剪弄的报纸投进无人售票箱里。
虽然我投币的手没颤抖,但心中却哆嗦了一下,幸好那司机只是疑惑了一下就吆喝着其他的乘客。
当车子开起来时,她向我笑了,不知是否车子颠的缘故,我第一次发现她的笑可用花枝乱颤来形容。
到了地铁站我用我俩剩下的两块钱买了一张车票,然后对着她神兮兮地说:
“我既然能不要你走着回来,你可要以身相许呵,你等一会要搂着我的腰,而且要紧紧地搂着。”
望着她一脸愕然的神态,我这才得意地补充道:
“别紧张,就只在过闸门的那瞬间。只有一张车票当然只能一个人过,但我俩可以一加一还是一。”
她听了对着我灿然一笑,突然一把扑了过来,紧紧地搂着我,虽然此时还没到闸门口。
我突然觉得全身很热,不论是跟她接触的地方还是没接触的地方,就跟一块通体烧红的炭一样。
然而,我全身上下却没有半点的难受,甚至很舒畅,只想这炭火就这样永无休止地燃烧下去。
所以,我走的虽是人步,但步的距离却跟蚂蚁走的差不了多少,甚至有时我根本就不想动。
可是,无论我多想走慢一点,但闸门还是出现在我面前,一闪而过后身上的火热也随之而逝。
我突然有一种失落,好像不知谁把我的灵魂从体内抽走一样,剩下的只是虚无与空荡。
地铁里人并不多,空调就更显强劲,然而她的脸又出现了晕红,像是抹了红粉一样想褪也褪不掉。
出站后,她搂着我的手并没放开,轻轻地在我耳边说道:
“我···我现在已很累了,你能否将我背回去?”
她说完将脸伏在我的背上,我知道如果我拒绝的话她定会很失望,就算猫没人宠它它也会很失落。
所以,我已将她背在身上,她并不重,甚至有点轻飘飘,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兴奋令我有这感觉吧。
她许久都没说一句话,但我知道她并没睡着,因为我感到她的呼吸时急时缓,根本就是心情的激动。
我呢?闻着她的馨香,受着她柔丝的轻拂,心中同样是汹涌澎湃,遐思万里。
我背上背的虽是人,但其实背的是我的希望,或者是我对她的那份朦胧感觉~相厮相守的向往。
站口离我俩的“家”并不远,几分钟就到了,但这也足以令我头上冒出细汗来,层叠如列障。
她已下来了,拿着洁白的手帕轻轻地拭擦着我脸上的汗珠,那种温情柔意令我恍如梦中。
“你真是很特别!以我的观点认为,现代人如果还用手帕的话那实在罕见。”
“手帕等于特别?这是逻辑还是定理?我倒愿听其详。”
她口中虽说着话,但手上并没停下来,然而力度却是小了。
“其实这既不是逻辑也不是定理,只是我个人的观点,当然观点并不一定都是对的。
我这样说乃是有感而发,它令我想起了爱情,现代人对爱情的态度。
现代人对爱情的追求已没有古时的那股执着,或者说根本就很随便,随便得放弃爱情就如放弃纸巾。
当然对爱情本身也没耐性,一次见面二次拖手三次亲吻以后的我不说你也明白。
如果那次出现了问题,不好意思,时间宝贵,我们不如就缘尽于此吧。
所以,现代的爱情已没了以前那种刻骨铭心的烙印,像纸巾一样,擦一擦就没火花了,只好扔掉它。
你能保留用手帕的传统,我想你也会有着传统的爱情观,这在古时是普通的,但在现在是特别的。”
“这的确不是逻辑或定理,然而它虽是你的观点但倒也有点哲学的味道。
然而用手帕来比喻爱情却是渎犯了纯洁的爱情,难道你还能从这手帕中寻到半点爱情的迹痕?”
她说罢将手帕在我眼前扬了扬,除了我的臭汗味外果然闻不出半点的爱情味道,我不禁笑了。
原来,爱情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,绝不是用些什么东西就可比喻或比拼出来的。
周未总是令人向往的,因为是它才令我俩有时间坐在北郊的一个沙滩上。
这个沙滩并不太大,这是自然的,江边的沙滩能有多大,你总不会对鱼缸里鱼的大小发出惊呼吧。
然而,我俩却喜欢上这,因为这里的沙很干净,更重要的是这里很安静,根本不曾见到人的影子。
所以,我俩也半天没说半句话,安安静静地让夕阳温暖着我们的心房和江风抚摸着我们的身子。
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完美,若说有美中不足的也该只有林中的鸟声,但听起来倒也悦耳。
“慰安,你能否帮我到路口的小店里买支可乐,不是我懒,只是晚霞太美了,我舍不得走开。”
我说此话自是有我另一种深意的,她回来时她已强烈地感受到我的深意:
“怎···怎么回事,怎么沙滩上突然会有这么大的羊?”
她神情的惊骇连手中的可乐掉在地上都不知晓,只是呆呆地望着沙滩上画着的羊。
“这是我送给你的小礼物,羊,用脚画的羊,你喜欢这只羊吗?”
我微笑着说,甚至有些得意,能给人意外和惊喜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。
半晌,过了半晌,她终于回过神来,双眼含着微笑地对我说:
“多谢!你说到做到并没有食言,我真的很感动,既然你是脚做的礼物那我也用脚收这礼物好了。”
她弯身脱掉鞋子,她的脚很白,用白壁无暇来形容绝没夸张的成份,别人说素腰聚情,那她的脚呢?
该是银足惹风吧,因为她伸开双手,光着脚顺着那羊的痕迹轻轻地走着时像一片云彩一样的轻盈。
看着看着时,我又突然觉得她比天上的彩云更轻盈,也更灿烂,也许是她已幻作我心目中的彩虹吧。
她终于将礼物收了,甚至连天上的云彩也收在身上,因为在霞光中她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美丽。
她有些轻喘,但却充满着欢欣地对我说:
“你的礼物虽然简单,甚至不能让我带走,但很特别,我相信它将会长驻我心。
我现在已收了你的三件礼物,我都很喜欢,因此我现在突然很想知道你的第四件礼物是什么?”
我听了心中舒畅得就跟皱了的衣服给烫顺一样,但我仍摇了摇头道:
“我现在也不知道,但就是知道了我也不会告诉你。
留着一份神秘总是比明白的好,西藏就是因为神秘才让世人如此神往。
你那么早就想知道莫非是怕我的下一份礼物长着翅膀自己会飞掉?”
回去时江边的夜景实在美丽诱人,所以我俩都同时在饭馆里坐了下来,原来人留美景美景也留人。
享受着江风的温柔和感受着啤酒的清怡的同时,我眼前的夜景慢慢变成了一幅模糊着的山水画。
我知道不是美景醉人就是啤酒醉人,但无论是那种醉法,都足以掏出了我埋在最心底的话。
“世上危害力最强的是无形的物质,而并不是有形的物体。
钢铁虽硬,但可以融掉;老虎虽凶,但可以杀掉;子弹虽快,但穿不透墙体···
所以无论这些东西有多硬,多凶,多快,但人们都有法子对付它,因为它有形有踪的就总有缺点。
火,因物而窜高,因风而变形,并没固定的形态,所以人们很难扑灭它,有时甚至要花数月的时间。
风,人们看不到它,它来无影去无踪,只能从其它物体才看到它肆虏的足迹,所以人们很难防范它。
地震,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形状,但它的破坏力最强,因为无论你逃到那都逃不出它发威的范围。
同理,对人伤害最深的不是各种内外病痛,而是心病,心病决非是中西药所能医治的。”
我又喝了两杯啤酒,但我觉得冰冻的啤酒到了我肚里根本就不能凉彻我的心,甚至酒更令我激动。
“我说这些其实是想说我的故事,也是我的一个心病,它是我有生以来所受的最重的一次伤痛。
我遇上了一个女孩,我第一眼就喜欢上她,我为她做尽了我百分百的精力和花尽了百分百的心思。
然而,结果却是···”
我口里清楚地说着我的故事,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她可爱的影子,但热泪却早已模糊了我的眼晴。
那实在是我最为刻骨铭心的日子,我每每想起它的时候我的心情总是特别地激动。
现在激动的不但是我,还有她,我虽然已看不清她的脸,但却明显地感到她语调的哽咽:
“你···你的故事很感人,甚至有点凄美,我真的给你感染了。
然而,火烧完了物体也就灭了,风吹久了终会停,地震无论怎样震但地仍是地。
所以,你的心病终会痊愈,因为时间会将你的热情消耗、***磨平和心情麻木。
虽然如此,但我知道你的心中将会留下创伤的疤痕,一记永不消失的烙印···”
她的安慰似是柔风轻抚着粗糙的石头,作用并不太,我仍是喝了很多酒,也流了不少泪。
她沉默了,只在一旁静静地陪着我,既不劝我也不陪我喝,甚至存在的意义只是她的影子。
我知道我已醉得很,因为我竟对着闪烁的江面问她为何天上的星星都掉到江里去啦?
她并没回答,但不知是痛心还是心痛,我记得最后看着她时她正用手帕拭着她眼角晶莹的泪珠。
至于怎么回去我是更不知道了,那感觉像是云,所以回去后我就给太阳拍散一样躺在床上不知何踪。
早上醒来时我大吃一惊,因为我发现我竟然是躺在她的床上,昨晚该没做错什么事吧?
她精神很好,但瞧着我的神色有些古怪,甚至从端重中透着一丝羞色,这更令我感到羞愧。
“对···对不起,昨晚我喝多了,也许说错了话做错了事,我不敢你原谅,但这不是我本意。”
我喁喁而言,然而心里的难堪甚至令我的头低得比脖子还低。
“这有什么?有伤心事的人难免都会借酒消愁,虽然最终愁末远去忧又来。”
“但是···但是···”
我不敢说下去,也不想太明言,只是用眼角瞄了瞄她的床。
她见了忍不住“卟噗”一声笑出来,左瞧右瞧上看下看直把我脸色涨红浑身不自在才嘻笑着道:
“嘻嘻,你昨晚也真不老实,一回来就倒在我床上呼呼而眠,死猪一样我左推右拉都弄你不下来。
实在没办法,我只好到你床上睡了,闻着总有一股怪味,睡得真是裂了缝的鼓~不香(响)。”
我心中“哦”了一声,肩上如释重负,然而心中却又似有一丝淡淡的失落。
那日历已撕掉不少,想着一张不剩就是分手之期时,我就特珍惜我跟她在一起的分分秒秒。
然而,无论我如何珍惜,但时间还是一点都觉察不了我对它的眷恋,一分一秒地从我身旁滑过。
我心情有些沉重,更带点忧郁,因为我已将她当成了好朋友,但是也许她从此会在我生命中消失。
我有些不甘,难道我跟她的结果就只能是拥有流星刹那的灿烂,而不能占有月亮的那种永恒?
今天是二十七号,星期五,再过完这个周末我俩约定的期限就到了。
想到这我的心就往下沉,特别是接到她电话告诉我今晚要早点回来,不要超过九点之后。
她不会有什么事吧,怎会今晚一定要我早点回来?
我假设着各种可能,然而各种可能的结局都是让我替她担心,所以很想能飞到她的身边。
上班的时候,我第一次感到有和失眠一样的心绪不宁,整天在想着我和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
很清晰,也很麻乱,反反复复交织在一起,不断地冲涤着我的脑海。
我的心情很沉重,庆幸的是离下班的时间已不到半小时,所以我的心情又慢慢开朗或是明快起来。
然而,不知是上天捉弄我还是我冒犯了上天,正在此时我接了一个电话,令我终生都遗憾的电话。
“喂,你是安慰吧?我是义汉公司,你做的电脑系统出了点问题,请下班后过来一趟。”
“今晚我有事,能否改天再去?”
“不行,现在已是月末,那些报表明天一定要交,现在可没过三个月的维护期。”
他的语气像是用锤子敲出来的,“咣咣咣”的硬得很。
“今晚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,明天,明天我一定帮你弄好。”
我近乎哀求的语气令他的语气也软了下来,商量着道:
“你也该体谅我的难处,也许用不了半个小时你就弄好了,难道连半个小时都抽不出?”
对,也许就只花半个小时,我就答应他吧。
“好···吧。”
但我知道口中说好但心里却一点都不见好,就跟首长问你“累吗”你答“不累”一样的矛盾。
下班到那后才发现系统并没什么问题,有问题的是那操作系统,它瘫痪得已成了一堆烂泥。
如果不是种花烂泥是没什么用的,所以我只好把操作系统和相关的程序数据重装一遍。
这本来没什么难度,就跟骑摩托车一样,只是加加油门转转弯而已,又不用你扛着摩托车跑。
然而它却耗去了我的不少时间,当我做完这一切时时间已毫不给情面地过了八点。
我的心有些焦急,“咚咚”地以最快的速度冲到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。
然而一切都似是针对着我,天突然下起大雨来,骤雨非但把行人弄个措手不及,也使汽车晕头转向。
所以,街上的交通很乱,非但乱,简直可用险象环生来形容这种状况。
车子走得很慢,既是路滑的缘故也是车多的缘故,直把我的心和雨水同样的冰凉。
窗外是那样的模糊,模糊的不但是眼前的景物,也把我的思维给模糊着。
我喁喁而言,也是反反复复而言:
“她现在不知怎样?我能在九点前赶回去吗?···”
这一趟车走的路并不多,花的时间也不漫长,但我却觉得比我以前任何一次坐的都要多,也要长。
也许是因为我的心思在挣扎着的缘故吧,挣扎着的生命除了对生命的渴求外更多的是对恐惧的无奈。
终于,我终于看到了我俩的房子,但我并没半点兴奋,甚至心情有点沉重,因为已是九点过九分。
我突然似是看到了她,一辆缓缓驶过的小车有一团白色的影子朝后望着我俩的房子,既朦胧也清晰。
“是她么?”
我心中一震,然而就那么迟疑了一会,那小车已化为了雨点离开了我的视线。
我“咚咚”地跑上楼去,还没到“家”就大声地喊着她的名字。
然而,通道里除了自己“咚咚”的脚步声和带点寒意的狂风外就再没其它的声音。
我知道我已迟了,非但我俩的房门没开,甚至连房前那盏长明灯也灭了。
那盏长明灯是我俩在一起的守护神,我每次回来看到它时都感到一股难言的暧意。
但现在我心中犹存的一点希望破灭了,甚至连心都破碎了,因此我感到这个夏夜比腊月的寒冬更冷。
房子里很整洁也很整齐,但少了不少东西,那是她的物品,所以看着又觉得有点冷清。
冷清不是因为少了些东西,而是因为她已不在我身边,这是孤独的反应,也是心灵寂暮的必然。
我麻木迷乱的目光突然有了点精神,那是因为我的目光捕捉到一条红丝巾,红彤彤的很艳也很漂亮。
我走过去拿起它的同时看到了一封信,是她写给我的信。
“安慰:
你好!
现在已是八点三十分,但你仍没回来,我的心只感麻乱至极,不知如何是好?
因为今晚我就要离开你了,没在电话里告诉你实在是我的最大失策。
我知道你肯定是被麻烦的事缠着你,要不就这大雨让你遇上了意···外。
意外?老天求求你千万别,你已不让我见上他最后一面,难道你竟忍心他不幸?
看看窗外,但仍没你那熟悉的影子,我虽不愿意,但也只能提笔来诉说啦。
今天我除了收拾东西外,大部分的时间里就是静静地坐着回忆起我俩在一起的日子。
这段日子并不长,在漫长的人生里程中甚至微小得可以用白驹过隙来形容。
然而,这段日子却又是我最难忘的日子,绮丽得根本就跟滔滔长江中的三峡一样。
也许你很平凡,但你为了我却已尽你所能,所以我已感到很满足。
因为这不能拿别人来比较,而且又如何能比较完,一山还有一山高呢。
所以,我很感激你,感激你这段日子以来为我所做的一切。
这段日子我过得很快乐,也很幸福,真的。
还记得在地铁的时候吗,就是我紧紧搂着你的那一次?
虽然你的身子不算高大,但我伏在你背上时又觉得很安全手兴朴幸恢挚梢揽康母芯酢?br>
那段路并不长,甚至那段路根本就不是我所走的,但我却觉得那是我所走的最幸福的一段路。
那是我跟你最亲的一次,然而,以后我也不知我俩还有没有机会在一起啦。
我要说声对不起的是我从一开始就隐瞒了我的真相,我身体的真相。
我上了大学后就得了癌症,癌症不用解释你也该知道那是死亡的代名词。
这就是我身子冷的原因,也是那晚我突然消失的原因,叫你担忧只能现在才说声抱歉啦。
父母为了我的病东奔西跑,本来挺享福的人却因此憔悴不少,年龄似是突然催生了好几年。
我见此只好强起笑容说:
不用担心,生死自有天命,你给女儿一个月时间活得开心就行了。
他们无奈却答应了我这个请求,但仍要我每天都吃药,而他们继续四出寻医。
今···今晚,我在他们的安排下就要到加拿大治病去了。
没认识你之前,我觉得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机会,现在却陡然觉得有百分之八十的希望。
然面,生命就真的会按百分比例的方式生存下去吗?
我现在觉得很孤独,虽然我父母现在就在我身边。
也许是因为你不在我身边的缘故吧,老天怎么就不让你赶回来让我见你最后一面?
还有你那最后的礼物,难道就让那礼物成了梦想的恭品?
我留下了一条红丝巾,那是我送给你的礼物,唯一的一件礼物。
你有看过《红丝巾》的故事吗?它是很感人也很凄美的故事,我送红丝巾也是有这个深意的。
一年,再过一年,如果我能好的话,你会将那红丝巾挂在我们房前的那棵白兰树上吗?
现在已经九点过三分钟,虽然我想再等下去,但我父母却催着我要走,因为飞机可不等人。
望了望窗外,雨还是很大,但是这怎比得上我内心的伤痛和遗憾大。
我不想也不愿,但我还是要说声再···见!
慰安”
我知道她写这封信时的心情定是激动不已,因为她的字迹越来越草,跟炊烟一样越往上越见清淡。
我已泪如雨下,整个人呆了半晌这才发疯似的冲到楼下拦了辆出租车直奔机场。
我在车子里思索如潮,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她说,但是我还能亲口对着她说么?
终于赶到了机场,但我知道我还是来迟了,缓缓驶出跑道的客机正无情地碾碎我仅存的一点希望。
那播音员昔日甜美的声音今天就像是一个狠毒巫婆的咒语,就是她将客机推上了夜空。
我只能呆呆地无助地看着客机消失,消失在夜空当中,也消失在我心灵间。
然而她在我心灵间并没消失,而且永远也不会消失。
我脑海间突然变得空明起来,似从遥远之处飘了首歌出来,这就算是我送给她的最后一份礼物吧:
江南好,风雨飘飘把它摇,风失雨难好,泪雨空鸣。
人间美,天地悠悠为它造,天亡地凄美,冷地孤清。
世道明,日月莹莹是它灯,日暗月无明,云月堆影。
亲情意,父母殷殷合它凝,父去母寒意,寡母悲声。
千古情,你我声声共它唱,你别我空情,遗我苦伶。
······
歌声已消失在夜空中,但我不知道它有没有顺着气流飘扬到那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?
然而,我却知道我的心已经开始下雪,和加拿大一样皑白洁莹的雪!